第832章 齙牙
一見這架勢,這人轉身便跑。
啞巴抬腿就追,燕子急忙攔住啞巴,大聲說道:
「我的祖宗呦,你惹誰不好,偏偏惹他們」
見對方跑遠,燕子才鬆開啞巴。她着急忙慌的衝着我們說道:
「你們快點收拾東西,準備跑路吧!」
「跑路?」
我有些奇怪的看了燕子一眼。
燕子依舊是一臉的焦急,一邊朝着酒店裏面走,一面解釋說:
「你們不了解,這個鎮上的飛車黨,大都是阿豪豪哥的人」
「他是飛車黨的頭兒?也是搶劫的?」
我追問了一句。
燕子搖頭。
「不是,是飛車黨的這些人,每個月都要給豪哥上交一定的費用。他們出事,豪哥會幫他們擺平」
「那豪哥是做什麼的?」
「豪哥是外省人,來莞城十幾年了。什麼都做,開賭場,收保護費,走私汽車,養小妹。只要賺錢,就沒有他不做的。豪哥極其愛錢,為了錢什麼都敢做。用他的話說,讓他賺錢的就是他親爸爸。擋他財路的,就是他敵人。在這個鎮上,沒人不知道豪哥,也沒人敢惹豪哥」
說話間,我們已經進了酒店裏。燕子着急忙慌的說道:
「初六,你也別怪燕姐膽小怕事。我就是個媽咪,沒本事沒背景,賺點皮肉錢養家餬口。我是真保不住你們,你們快走吧」
我當然不可能怪燕姐,回去收拾了一下東西,便準備到大堂去和燕子道別。
剛一到大堂,就見燕姐正戰戰兢兢的站在休息區。
眼睛看着窗外,神情絕望。
我順着燕姐的目光,看向窗外。
這一看,我才明白燕姐絕望的原因。
就見酒店門口,站着足有二三十人,這些人手裏拿着各種傢伙。
看着他們手中的傢伙,我才明白北方和南方混子還是不同的。
在北方,一般都是以砍刀和木棒為主。
但這些人的手裏,竟然還有長長的關公刀和紅纓槍。
這感覺不像是街頭鬥毆,倒更像是上戰場。
「完了,完了!這回真完了,齙牙輝來了」
燕姐絕望的嘟囔着。
「齙牙輝是誰?」
「阿豪的一個小弟,人陰險又狠毒。曾把我們這裏一個欠他們賭債的小妹,活生生的砍了一百二十多刀。最後送到醫院,連醫生都沒辦法下手縫針」
說話間,酒店大門被人推開了。
七八個打手簇擁着一個男人走了進來。
這男人個子偏矮,身材幹瘦。
穿着背心短褲,腳上則是一雙人字拖。
嘴裏還嚼着檳榔,一進門便隨口吐出鮮血一樣的通紅唾液。
最引人注意的,是他嘴唇都包裹不住的,焦黃泛黑的齙牙。
看來這人,應該就是齙牙輝了。
燕姐急忙上前,卑躬屈膝的打着招呼說:
「輝哥,您怎麼來了?」
齙牙輝呲着他的齙牙,看了看燕姐身邊的我們,半笑不笑的說道:
「聽說燕姐養了幾個關東仔,專門搞我們的人。我來認識一下啦」
燕姐嚇的夠嗆,她連連擺手,說道:
「不,不,不,不是我養的」
看着燕姐嚇成這樣,我便直接說道:
「和燕姐無關,有事和我說吧!」
齙牙輝上下打量我一眼,嚼着檳榔,用他含糊不清的普通話說道:
「剛來莞城的?」
我點了點頭。
「剛來就敢動我兄弟,膽子不小嗎?」
我沒說話,冷漠的看着齙牙輝。
反倒是啞巴瞪着齙牙輝,磕磕巴巴的說道:
「就,就干,干他了。你說
第832章 齙牙
 重生黑熊 一代古武大師李霸天,因為一顆隕石之珠被迫自爆,卻巧合開啟了其中的外星科技超智能生物進化器CP9,重生成一隻黑熊。在進化器CP9的輔助下,李霸天不斷激活各種基因,擁有神奇的血脈能力,並且以黑熊之
重生黑熊 一代古武大師李霸天,因為一顆隕石之珠被迫自爆,卻巧合開啟了其中的外星科技超智能生物進化器CP9,重生成一隻黑熊。在進化器CP9的輔助下,李霸天不斷激活各種基因,擁有神奇的血脈能力,並且以黑熊之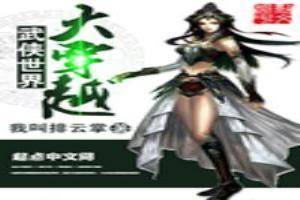 武俠世界大穿越 一位武學天賦極高的現代散打高手,穿越於各類武俠世界中,一步步成為顛峰強者的故事!
各位書友要是覺得《武俠世界大穿越》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QQ群和微博里的朋友推薦哦!
武俠世界大穿越 一位武學天賦極高的現代散打高手,穿越於各類武俠世界中,一步步成為顛峰強者的故事!
各位書友要是覺得《武俠世界大穿越》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QQ群和微博里的朋友推薦哦!
 爺是病嬌,得寵着! 父親總是說,徐紡,你怎麼不去死呢。因為她6號染色體排列異常,不會餓不會痛,還不會說話。蕭軼博士卻常說:徐紡,你是基因醫學的傳奇。因為她的視力與聽力是正常人類的二十一倍,奔跑、彈跳、臂力是三十三
爺是病嬌,得寵着! 父親總是說,徐紡,你怎麼不去死呢。因為她6號染色體排列異常,不會餓不會痛,還不會說話。蕭軼博士卻常說:徐紡,你是基因醫學的傳奇。因為她的視力與聽力是正常人類的二十一倍,奔跑、彈跳、臂力是三十三- 位面養成系統
- 邪王追妻:廢材逆天小姐
- 我全家都是穿來的
- 七根凶簡
- 天國遊戲
- 主神大道
- 陰陽鬼術
- 萬界聖師
- 最強戰神
- 星辰之主
- 從黑袍開始當海王
- 重生八零,二嫁硬漢老公寵斷腰
- 全職法師:開局用暗影捆綁穆寧雪
- 玩家重載
- 地球編劇在無限
- 羅天九道天書全集
- 宿主
- 最後一個道士
- 張奕末世重生免費閱讀全文